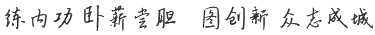|
1958年9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先下放锻炼到四川资阳当了一年农民,获得“五好”奖状;回所后受命到湖北沙市,研究危害荆江大堤的白蚁地下巢穴结构和位置,以求消除“千里金堤毁于一穴”之隐患。该种白蚁只在黄昏暴雨时才出巢“婚飞”,我们就在堤岸搭帐蓬露宿,傍晚冒雨观察其飞出交配再入土建窩详情,白天则钻在堤坡草丛中寻找并标记白蚁地面取食盖的“泥线”(蚁路),研究其活动和建巢规律。这样每天逐平方米查几公里,或跟隨民工挖蚁巢测量记录其结构,劳动量很大。当时正值缺食岁月,每天仅几两粮,无油无肉,幸亏堤旁有个瓜园,我们天天买西瓜充饥。如此经1960-1961两年野外调查,在蔡邦华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黑翅土白蚁的蚁巢结构及其发展》《长江大堤上黑翅土白蚁的地面活动与其巢位的关系》2篇研究报告,发表于《昆虫学报》第14卷,是为我的处女作。之后,在马世骏教授指导下,做“高温对粘虫发育与生殖的作用”研究。粘虫是当年在我国南北方广泛危害水旱作物的重大害虫,急需掌握其发生规律。为此,我和同事们周周7天、日以继夜地进行实验观察,曾累得“神经衰弱”到香山疗养。这样辛苦4年完成了4个虫期的全部实验,可惜只发表了卵期的论文,而因“搬迁”和“文革”耽搁,部分实验记录散失,未能写出虫、蛹、蛾的实验报告,是终生遗憾。
 |


1978年中科院组建南、中、北3个“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我作为科研骨干同时也照顾家庭困难,于次年奉调到“中科院桃源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后改为长沙,现名亚热带农业生态所)。起初我已回归农业害虫研究,1982年因长江南北广泛暴发褐家鼠灾害,应湖南省科委要求,我重新承担农业鼠害防治技术研究。开头所里只配给我1名大学毕业生,后来隨着承担省、院任务,扩展为近10人的大组。我们从组织农村大面积灭鼠入手,逐步查明南方害鼠种类和生物学特性,提出“全栖息地毒鼠法”和“复方灭鼠剂”等整套技术,由桃源、长沙试点,再到省内多个县,结合当地政府,组织县、乡级规模灭鼠;然后到桂、皖、川、鄂、赣、沪等地作技术示范推广,都取得高效、持久、安全、经济的防治效果。1992-1993年更与中科院昆明分院合作,在乡级试点基础上,组织云南思茅地区7县同步灭鼠,得到当地盛赞,授云南省科技进步叁等奖。

依“任务带学科”方针,我在长沙所主持农业害鼠生态与综合治理研究。1982-2000年间,本科研团队在学术会议和书刊上发表论文114篇(含科普13),并与中科院动物所同事合作《害鼠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1996)、《农业重要害鼠的生态学与控制对策》(海洋出版社,1998)及《Rodent pest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in China.》(见《Ecologically-based Management of Rodent Pests》Pp261-284,为中澳合作英文专著第12章,1999.)等专著,经鉴定、验收的科技成果16个,获中科院和省级科技进步奖叁等奖5个、贰等奖3个,参与国家科技进步贰等奖1个。2000年以来,我的学生们接续工作,既持续了洞庭湖东方田鼠种群生态研究,还开展了四川汶川地震灾区鼠情检测、西藏农业害鼠调查等项目,除陆续发表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洞庭湖区退田还湖工程后小型兽类群落演替》(张美文等,科学出版社,2016)等多本专著。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本人1997年退休后,先是受返聘指导博士研究生至1999年底;本世纪头十年,主要投入与国内同行联合主编《啮齿动物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2012年连出二版:其间,我还陆续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近十年则着力科普文章写作,在中科院网络化科学传播平台“科学新语林”开个人专栏《鼠族奥秘》,至今连同在所网站发的已逾60篇。而因写新疆鼠害,联系到博州农技推广中心的鼠防专干,得知她积压着十几年害鼠调查数据,为指引其做科学总结,我连续数年通过互联网作学术指导,她今已写出多篇学报级论文,并增强了坚持灭鼠技术岗位的信心。
 |
值此新中国和中科院建立70周年之际,回顾我在中科院61年历程,憾未能有大的建树,但我始终将“祖国需要”为使命,遵从组织安排积极工作,先后在3个所主持完成中科院、省和国家的重大、重点、攻关、科学基金及国际合作课题12项,参与8项(其中退休后5项),总计执笔及与人合作正式出版学术论文70篇、中文专著4本、科普作品80篇(件),组建的科研组9次评为“先进集体”,本人10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教师等。1987年湖南省授“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2年10月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可以说,我忠实地践行了“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志愿。
(2019,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