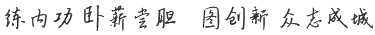2020年初,一场疫情打乱了整个世界的节奏,这篇早该见报的稿件也一再推迟发表。
早些时候,本报记者前往洞庭湖采访时,计划的只是一个探讨湖区生态、人鸟关系的选题。搁置至今,文稿反而有了更多的解读空间。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句话,永远不过时。
——编者
蛙泳吗?以后会天天见,喝杯啤酒,交帮朋友。”
视频里,一只江豚在浪里翻腾。3月3日晚上,陈振华朋友圈的“画风”突然变了。此前,他镜头里的主角都是鸟。
“想打群架”的灰鹤、“互相较劲”的黑鹳与苍鹭,优雅侧踢的小天鹅……陈振华的“诗意栖居”在最近两个月尤其让人羡慕,与鸟为伴,出入都不用戴口罩。
2月28日,告别朝夕相处近10年的横岭湖自然保护区青山岛管理站,陈振华调任新化沟江豚监测站站长。不过,无论对他来说,还是对洞庭湖来说,“人鸟鱼水”的故事还在继续。
作为最容易监测的指示性物种之一,候鸟的种类和数量被视为湿地环境质量的标志。今年1月中旬,洞庭湖开展越冬候鸟同步调查,共记录候鸟24万多只,较上年同期小幅增长。
从早期30万~50万只,到不足10万只,候鸟数量经历了一次“v”型回归。
洞庭湖自古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人类活动频繁。1982年,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成立,随后20多年间,洞庭湖又成立了大小3个保护区。在这里,无论有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人与自然如何相生相息,始终是一个要面对的课题。
湖水退得越来越快
横过湘江一片漆黑的江面,湖洲浅滩分割出弯弯绕绕的水路,夜里看起来差不多是一样的。夏玮尝试了很多次,仍然没有找到通向青山岛的唯一通道——沈家坪,他驾驶的快艇几次险些搁浅。
2019年12月初的一个夜晚,时任横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分局局长的夏玮,带着记者前往横岭湖中的自然孤岛青山岛,造访陈振华。
57万亩的横岭湖是洞庭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大小24个常年性湖泊和3大片季节性洲滩组合而成,丰水期与洞庭湖碧波相连,枯水时节则与之季节性分裂。“现在湖水退得越来越早了,”夏玮感叹着水上“行路”之难,“如果不是当年围湖造田失败,说不定青山岛早与陆地相连了。”
1978年,湘阴县提出“再造一个湘阴”口号,举全县之力围垦横岭湖,计划把其中40万亩水面改造为农田。为了支持参与建设的劳动力,那段时间,县里的所有猪都被“调”去犒劳修堤大军。
当年夏天,刚建成的堤坝就被资江的洪水不客气地冲了个口子。
“再造一个湘阴”计划流产,对洞庭湖的围垦却一直没有停止。“洞庭八百里,玉盘盛水银”是宋代词人姜夔笔下的洞庭湖;600年后的清代道光年间,洞庭湖面积为6000多平方公里;到1958年,这一数字急剧减少为3100多平方公里,原本完整的“玉盘”已经“掰”碎,呈反写的“L”形。
到今天,洞庭湖湖面海拔34.5米时的水面面积为2820平方公里。
“高强度、高频率人为干扰,湿地格局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谢永宏谈到近10年来洞庭湖之变时,递给记者一本《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估》,“研究数据里面都有。”
快艇惊险靠岸,“岛主”陈振华早已等候多时。
青山岛面积不过11.2平方公里,却有鸟类200多种,植物300多种,是洞庭湖内具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的区域。2003年,湘阴县横岭湖县级自然保护区晋升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6年,湘阴县林业局保护区管理分局成立,建立的第一个管理站就在青山岛上。
2010年陈振华上岛时,管理站没有自己的地盘,只能借用当时乡政府的办公室,这一借就是7年。作为站长,他的所有装备只有一台单筒望远镜、一本观鸟手册。那几年,此前一直从事林业工作的陈振华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看鸟、认鸟,“没人对管理站有要求,管理站也要求不了别人。”
靠湖吃湖,和保护区管理分局成立差不多时间,采砂业在湘阴县兴起,并很快贡献出县财政70%左右的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可这后面有个‘尾巴’,”夏玮用背书的口吻说道:“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护区工作人员对侵入保护区内的采砂活动进行制止,对方往往会以条例中的“尾巴”来搪塞。
因湖而设的机构有十多个,“作为湿地管理机构,我们是唯一没有执法权的。”夏玮说,成立后近10年里,管理局顶多是个“守望者”的身份。
水是核心要素
陈振华经常散步的路上,会遇到好几片满是柚子的土地:屋前柚子树结果了,主人已举家离岛,重量超标的柚子一个个掉落,再一个个腐烂。
湖南最后一个渔村青山岛已经没什么人了。每家每户都有的渔船,现在多数反扣在门前的小坪上,成了摆设。
因此,能在马路边遇到五六个人“扎堆”商量着什么,算得上稀罕事。
商议的焦点是一台渔船发动机,“这是村干部在对渔民的生产资料估值。”陈振华与几个人打过招呼,转身告诉记者。
作为长江禁渔计划的一部分和湖南省禁渔试点县,湘阴县自2019年12月10日起全面禁渔,渔民的相关捕捞工具要提前进行估价、上交,然后集中拆解和处理。
鱼是湖区最重要的资源,但过度捕捞使得湖区鱼类总量和种类都急剧减少。
争夺渔业资源的“战斗”一刻也没有停下,在湖区,曾经同时存在着多个“帮派”,洞庭湖至长江主航道连接处,一度也被分段承包进行捕捞。捕捞方式从传统的网、罾发展到拖网、迷魂阵和电捕。恶性竞争之下,湖区渔产的最低价格曾到了8分钱一斤。
2008年后,矮围在洞庭湖兴起。所谓“矮围”,就是在洞庭湖水域上人为筑成堤坝。丰水期,渔民通过投放饵料吸引鱼虾进入围子并滞留其中,到了枯水季节,保有湖水的矮围成了天然鱼池,供人打捞,直至抽干捞净。
夏玮亲眼看到过养殖户竭泽而渔的收获过程,“最小的鱼苗都被制成鱼干售卖,有时候一个晚上鱼虾产值就有三四万元。”
外滩围网、湿地围垸、洲滩开垦,竭泽而渔的“圈湖运动”,不仅使以鱼为生的候鸟缺少足够的食物,甚至对候鸟的栖息地也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饵料和化肥的投入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抽水、放水的行为则破坏了原有的湿地生态系统,加快湿地旱化。
在谢永宏看来,“洞庭湖中,最核心的要素永远是水。”
上世纪80年代,“湿地抽水机”欧美黑杨作为造纸用材林被引入洞庭湖区。在资本的推动下,到2006年,从滩涂到湖心,能种的地方都种上了。
高达95%的郁闭度,让欧美黑杨树下几乎寸草难生。更严重的是,挖沟抬垅的种植方式导致土壤含水量减少,加快滩洲旱化和植被退化,从而影响候鸟生存和栖息。
2012年和2013年,洞庭湖水鸟均少于10万只,是近年来的最低值。
慈场湖的“秘密”
夏玮把车直接开进了慈场湖,轮胎卷起的泥巴纷纷甩到了车窗玻璃上。
若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冬天的洞庭湖如茫茫草原,可以走人,也可以行车。
上任不到3年,夏玮把横岭湖每个角落摸得门儿清,为此,湘阴县领导送了他一个“湖里精”的雅号。
“领导要视察,都是我带路。”他对这个称呼似乎很认可。
在距离一片数千亩水面大约1公里的地方,夏玮把车停了下来。从他架设的单筒望远镜看过去,水面上栖息着数以千计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琵鹭。夏玮说,2018年冬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这里记录到4000多只同为二级保护动物的小天鹅。“是一只一只数出来的。”他强调。此前,因为矮围和欧美黑杨泛滥,湖里的小天鹅很多年都没超过1000只。
变化从2017年开始发生。当年4月9日,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岳阳。夏玮记得很清楚,当天,湘阴县的采砂作业就全面停止了。
距离湘阴县100公里,隶属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岳阳市君山区采桑湖镇,形势也在那一年发生突变。“镇上与私人签订的为期10年的渔场承包合同,只进行了不到4年就突然终止。”采桑湖渔场场长高元满回忆,很快,推平湖中矮围、禁止人工养殖、禁止捕捞等一系列通知先后下达,“渔场的主要工作变成了修复采桑湖生态。”
干涸的慈场湖中,被推平的矮围痕迹还清晰可见。自2014年起,湖南省政府就陆续出台文件要求清理洞庭湖中的矮围,可文件层层转发,责任逐级转移,最后落到的具体单位往往无力执行清理任务。“要不是出了那件事,根本拆不动。”
夏玮口中的“那件事”是震惊全国的“夏顺安案”。在沅江市南洞庭湖下塞湖等区域,以夏顺安为首的涉黑犯罪组织非法修建矮围,将湖洲改造成近3万亩的“私人湖泊”,进行非法捕捞、采砂活动。2018年6月,该事件被曝光,此后短短13天,危害十多年的矮围被彻底拆除。
当年9月,全面的矮围清理行动在洞庭湖展开。“夏顺安案”的震慑效应让清理变得非常顺利,夏玮说,很快,横岭湖自然保护区内48处非法矮围被拆除干净。
同年,根据湖南省政府下发的《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欧美黑杨清退工作开始展开。按计划,到2020年底,洞庭湖4个保护区内的39万亩欧美黑杨要全部清理。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拉开了政府对洞庭湖治理方略历史性转折。为守护一湖四水,近年来湖南共进行了五次专项行动,全面关停4个保护区内的砂石码头、清理矮围网围近150处、重判猎杀天鹅案……“人类终于选择了主动给大自然让路。”夏玮说。
干旱的冬季,在单筒望远镜里,慈场湖那片水域显得既珍贵又奇怪。
这是夏玮的“小秘密”,“过去这里是捕捞矮围,停止养殖后,冬日的浅滩正好成了候鸟的栖息地,我就悄悄把它留下了。”他直视着记者,用一种警惕而狡黠的眼神。
拆围与保围
相比于“矮围”,姚毅更喜欢“碟形湖”这个名字。
“在鄱阳湖人们都是这么叫的。”在去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小西湖生态矮围的路上,他这样说。
铲平矮围的风暴行动掀起后,一场“保围”与“拆围”的争论也开始了。
上世纪60年代,为血防灭螺,东洞庭湖修筑了大西湖、小西湖两个矮堤。“冬天水退堤现,它们就成了天然的浅水湖泊,是越冬水鸟的栖息地。”姚毅在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工作已有25年,现任保护区管理局总工程师。
多年前,他还在大、小西湖附近的采桑湖管理站工作时,就能见到白鹤、小天鹅、白头鹤等数以万计的珍稀鸟类在那里过冬。
当得知湖南省拟将洞庭湖中所有矮围一并拆除后,谢永宏急了。
“湖水退得快退得多,洲滩出露面积增大,功能性植被苔草面积也相应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矮围成了冬季湿地保水最好的工具。如果全部拆掉,会使越冬水鸟赖以生存的湿润泥滩及浅水湖泊等环境丧失,最终导致越冬水鸟种类及种群数减少,乃至灭绝。”在位于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三楼的办公室里,谢永宏不断举出在新的“江湖关系”条件下洞庭湖湿地保护与修复所面临的问题。
在日益脆弱的生态基础上建立“人鸟鱼水”和谐共存模式,谢永宏认为要系统梳理和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理念、机制都要科学,不能“一刀切”。
2018年,立下“严禁外包,严禁种养,严禁捕捞”的“最严”管理措施,湖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保留了14个生态矮围,青山岛上的围栏场矮围就是其中一个。1月中旬,陈振华还开闸放了一次水,“这里潜鸭多,水深1米左右最适合它们栖息觅食。”
作为“一岛之主”,每年进岛的“客人”有哪些,各自聚集在哪里,喜欢吃什么,陈振华都很清楚。白鹤偏食,只吃水生植物的根;小天鹅喜欢在浅滩吃水草的根;天鹅和大雁好养活,只要岸边野草的根茎就能饱腹……
说得来劲,陈振华还学起了苍鹭站在水中捕食的样子,“姿势很难看,一站就是近一个小时,”他把背一驼,脑袋下垂,双臂缩到背后,“但最后下嘴那一刻动作却极为敏捷。”陈振华努力保持着平衡,“所以苍鹭有个别称,叫‘老等’。”
除了家人,候鸟是他最大的快乐源泉。
目前,像青山岛这样的管理站在横岭湖自然保护区已增至7个。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洞庭湖中曾风光无限的芦苇站基本都已荒废。造纸厂早已不生产苇浆,弃收的芦苇一岁一枯荣,在土地和湖泊中分解、腐烂,成为又一个可能影响洞庭湖生态的因素。
芦苇综合利用,成了谢永宏新的研究项目。
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在采桑湖管理站中的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里,他的硕士研究生汪丽燕已经选好了自己的论文方向:芦苇再利用。
临时搭建的苇菌培养大棚中,放着塞满芦苇屑的袋子,已有不少食用菌从中探出了脑袋。汪丽燕正在用木屑等常规配方填充食用菌培养袋,“这是对照组,如果在同等条件下,苇菌品质更好产量更高,实验就成功了。”
成功,意味着洞庭湖的芦苇将有新的出路。
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才能最终平衡经济与生态的关系,这是各方正在达成的共识。
“我还不如湖里一只鸟”
与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相连的建筑,是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物馆,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巡回法庭也设在这里。
“这里审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我们渔场的承包案,现在还没结案。”坐在巡回法庭的旁听席上,高元满说,承包商手续合法,每年承包费370万元,合同突然终止意味着其将损失巨额承包费和渔场经营费用,“人家自然要讨个说法。”
与之类似,在洞庭湖治理过程中,欧美黑杨的清退也是一场博弈。
杨树生长周期为7至8年,2006年前后,大多种植户都以20年甚至30年为限承包洲滩。以每亩年租金20元计算,一位承包10000亩洲滩的大户20年的租金就达到400万元,按规定都已一次性缴纳。如今欧美黑杨无论大小都要在3年内全部砍伐,种植户既要承受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又难讨回剩余的租金。
过去两年,洞庭湖内已清退欧美黑杨超27万亩,但除了杨树特别多的西洞庭湖部分地区外,大部分种植户还没有拿到相应的采伐补偿。“种植户有情绪,工作开展起来确实有压力。”夏玮坦诚地表示。
同样有压力的还有高元满。自2017年以来,为恢复采桑湖生态,渔场村支两委已投入近120万元用于垃圾清理、鱼苗投放和藻类植物种植。同时,渔场还要出人出力严防非法捕捞和电鱼行为。“虽说环境好了人人受益,但长期只出不进,渔场村民也有意见。”
“我还不如湖里一只鸟。”夏玮不止一次听到湖区百姓发出这样半认真半开玩笑的感慨。
在人口总数达1000多万的洞庭湖区,生产与生态的矛盾始终都存在着,两难的局面甚至在各个保护区管理工作上也时有体现。
2017年5月,靠着中央划拨的“湿地恢复与保护”专项资金,青山岛管理站建成了站房。可烧钱的事,还有很多。
夏玮举例说,快艇巡湖一圈至少两个小时,每分钟油钱8元,摊上维护费用,出动一次就要1000元出头。“这还不算联合执法的公安、渔政等人力支出。”采砂、养殖、种植杨树等项目叫停后,湖区各地财政状况吃紧,但还是尽量“抠”出环境治理日常开销,“很不容易。”
摸清湿地资源家底,顶层设计生态补偿、协调的系统机制,这也是谢永宏的期待,否则,“鸟无远虑,湖有近忧”。
好消息是,从今年1月起,原隶属县林业局的横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分局升格为湘阴县政府直属单位,成立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夏玮担任副主任。“我们已经和县政府对接好了,很快政府就会委托管委会进行环保执法。”
难得的清净
“居然有人在濠河附近玩滑翔伞!”一见到姚毅,彭祥林就怒气冲冲地说开了,来不及卸下他背上几十斤重的摄影包,“简直就是跟鸟争地盘!我拍了视频,待会儿就微博曝光。”
彭祥林与姚毅相识多年,性格却大为不同。
相比于姚毅稳重寡言,彭祥林就像个随时能炸开的弹药,“我就是一个有时间有兴趣的民间环保志愿者,非要跟洞庭湖里的各种违法活动死磕。”
接受包括环保组织、环保志愿者在内的社会力量的监督,是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对洞庭湖治理的新姿态。彭祥林在微博上自称“洞庭湖鸟人”,一旦有志愿者发现了珍稀物种,或是遇到捕鸟、打鸟或干扰鸟类活动等非法行为,他就把相关政务微博统统“@”一遍。
事实上,作为全球主要的候鸟迁飞之路——东亚-澳大利西亚线路上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洞庭湖生态早就不止关乎中国政府和人民。
2019年1月在进行越冬候鸟数量同步调查时,姚毅发现国际濒危物种小白额雁的数量只有3000多只,而往年这一数字平均都在15000只左右。为此,姚毅与同事去了多个外省湿地,却始终没能发现大规模的小白额雁。
“这让我们又困惑又着急。”姚毅说,直到当年3月最后一次候鸟数量同步调查时,“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了14000多只小白额雁。”
让姚毅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在一次候鸟保护会议上,国际鹤类基金会创始人乔治·阿奇波博士特意走到他身边询问起这件事。“可见候鸟保护对中国而言,已是一种国际义务。”
根据部署,今年我国将基本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这意味着国内第一批以保护生态系统为目的的国家公园将逐步建立。姚毅对此很期待,洞庭有三宝,麋鹿、江豚和水鸟,“未来,洞庭湖就不仅仅只是鸟至如归的地方了。”
与彭祥林见面前,姚毅也去了一趟濠河。那是东洞庭湖观鸟的好地方。
接近黄昏,夕阳挂在开阔的水域之上,堤岸上架满了拍鸟爱好者的长枪短炮。成群的水鸟起飞,咔咔的镜头声就响成一片。
除此以外,几乎听不见别的声音。
“几十年了,洞庭湖从没像现在这样清静过。”姚毅说。